- œύΙΊΆΤΦω
”οΈΡΕΝ–¥ΫΧ―ßΡή≥§‘ΫΈΡΧε¬π
«≠ΡœΟώΉε ΠΖΕ―ß‘Κ÷–ΈΡœΒ ≥¬ ΌΫ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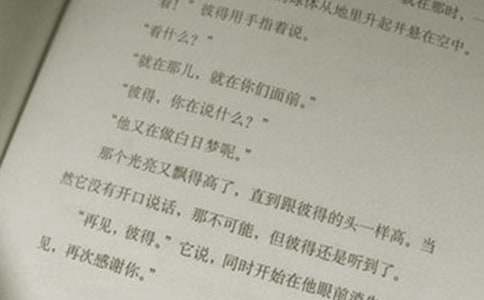
ΫώΡξΓΕ»ΥΟώΫΧ”ΐΓΖ12ΤΎΖΔ±μΒΡ–λΫ≠Β»»ΥΒΡΓΕΗΡ‘λ”οΈΡΫΧ―ß―–ΨΩΓΖΘ®ΚσΈΡΦρ≥ΤΓΑ–λΈΡΓ±Θ©ΒΡ“ΜΗω÷Ί“ΣΙέΒψΚΆ÷ς’≈ΨΆ «ΓΑ≥§‘ΫΈΡ±ΨΧε ΫΒΡ‘Φ χΘ§ΉΏœρ’ή―ßΥΦΈ§Γ±ΓΘΈ“Ο«Ά®ΙΐΖ¥Η¥―–ΕΝΖΔœ÷ΘΚ–λΈΡ «’κΕ‘ΓΑ“άΨίΈΡ±ΨΧε Ϋ»ΖΕ®ΫΧ―ßΡΎ»ίΓ±Φ¥ΓΑΑ¥’’ ΪΗηΒΡΖΫ Ϋ»Ξ‘ΡΕΝ ΪΗηΘ§Α¥’’–ΓΥΒΒΡΖΫ Ϋ»Ξ‘ΡΕΝ–ΓΥΒΘ§Α¥ΈΡ―ß–ά…ΆΒΡΖΫ Ϋ»Ξ‘ΡΕΝΈΡ―ßΉςΤΖ»»ñ”–Η–ΕχΖΔΒΡΘ§‘ΎΥϊΩ¥ά¥Θ§ΓΑ“άΨίΈΡ±ΨΧε ΫΓ±÷Μ «ΓΑ“ΜΗω¥Έ“ΣΒΡ±ΗΩΈΥΦΈ§‘ΣΥΊΓ±Θ§ΓΑ“ρΈΣ‘ΎΫΧ―ß ΒΦυ÷–Θ§»ΖΕ®ΈΡ±ΨΡΎ»ίΫ≤ ≤Ο¥Θ§»ΥΟ«≤Δ≤ΜΩΦ¬«ΈΡ±ΨΒΡΓ°Χε ΫΓ· « ≤Ο¥ΓΘΉς’Ώ“‘–ΓΥΒΓΔ¥ΪΦ«ΓΔ±®ΗφΈΡ―ßΓΔ…ΔΈΡΒ»Φ«–πάύΈΡΧεΈΣάΐΫχ“Μ≤ΫΨΏΧεΥΒΟςΓΑ≤ΜΆ§ΈΡΧεΒΡΉςΤΖΤδΡΎ»ίΫβΕΝ¬Ζ ΐ «œύΆ§ΒΡΘ§’β“Μ ¬ ΒΉψ“‘ΥΒΟς--Γ°ΈΡ±ΨΧε ΫΓ·Ε‘»ΖΕ®’β–©ΈΡ±ΨΒΡΡΎ»ί“ΣΫ≤–© ≤Ο¥--≤ΜΨΏ”–ΙφΕ®–‘ΒΡΉς”ΟΓΘΥυ“‘Θ§Γ°ΈΡ±ΨΧε ΫΓ·Ε‘ΈΡ±ΨΡΎ»ί≤ΜΨΏ”–Γ°“άΨίΓ·ΒΡ”ΑœλΘ§÷Ν…Ό≤ΜΨΏ”–»ΖΕ®ΫΧ―ßΡΎ»ίΒΡΓ°“άΨίΓ·‘≠‘ρΒΊΈΜΓΘΓ±–λΈΡ“≤≥–»œΉςΈΣΜυ¥ΓΫΧ”ΐΒΡ”οΈΡΩΈΘ§Φ«–πάύΉςΤΖΒΡΫβΕΝΘ§ΓΑ Β±«χΖ÷“Μœ¬ΈΡΧε±μœ÷–Έ ΫΒΡ≤ΜΆ§ «Ω…“‘ΒΡΓ±Θ§ΒΪΆ§ ±”÷ΧΊ±π«ΩΒςΓΑΒΪ≤ΜΡήΑ―Γ°ΈΡ±ΨΧε ΫΓ·ΉςΈΣ“άΨίΓ±Θ§“ρΈΣΓΑ’β―υΜα ΙΫβΕΝΥΦΈ§Ιΐ”Ύ’≠Μ·ΓΔœΗΜ·ΡΥ÷ΝΉ®“ΒΜ·Θ§…θ÷ΝΉΏœρΙ≈ΑεΓΔΫ©Μ·ΓΘΓ±÷Ν¥ΥΘ§Έ“Ο«“―Ψ≠ΟςΑΉΘ§–λΈΡΒΡ’β“ΜΙέΒψΚΆ÷ς’≈ΒΡ«ΑΧα≤Δ≤Μ «”οΈΡΫΧ―ß“Σ“‘ΈΡ±ΨΧε ΫΈΣ“άΨίΜρ≤Έ’’Θ§Εχ «≤Μ“ΣΈΡΧεΜρΕ‘ΈΡΧεΚω¬‘≤ΜΦΤΘ§ΨΕ÷±ΉΏœρ’ή―ßΥΦΈ§ΓΘΈ“Ο«»œΈΣ’β «ΦΪΕΥ¥μΈσΒΡΘ§»γΙϊ»ΈΤδΖΚάΡΘ§ Τ±ΊΕ‘”οΈΡΫΧ―ß≤ζ…ζ―œ÷ΊΒΡΗ…»≈ΚΆΈσΒΦΓΘΈΣΝΥΖά÷ΙΧ÷¬έΒΡΖΚΜ·Θ§Έ“Ο«ΫΪΧ÷¬έœό÷Τ‘Ύ”οΈΡΕΝ–¥ΫΧ―ßΒΡΡΎ»ίΓΔΡΩ±ξΖΕΈßΡΎΓΘ
“Μ
ΉςΈΣ¥σ―ß–¥ΉςΩΈΫΧ ΠΘ§–λΫ≠œ»…ζ±Ψ”ΠΕ‘ΓΑΈΡΧε « ≤Ο¥Θ§ Ε±πΈΡΧεΕ‘”οΈΡΕΝ–¥ΫΧ―ßΒΡ“β“εΓ±’β“ΜΜυ±Ψ≥Θ Ε≤ΜΒΞ”–Υυ÷ΣΘ§Εχ«“ «…ν÷ΣΓΘΩ…Έ“Ο«Ζ¥Η¥―–ΕΝ–λΈΡΘ§ΥϊΗχ»ΥΒΡ”ΓœσΨΆ «Έό÷ΣΘ§÷Ν…Ό «―πΉΑ≤Μ÷ΣΓΘ‘Ύ¥ΥΘ§Έ“Ο«”–±Ί“Σ÷ΊΧα÷±Ϋ”ΙΊœΒ”οΈΡΫΧ―ßΡΎ»ίΒΡ―Γ‘ώΚΆ»ΖΕ®ΒΡΈΡΧεΈ ΧβΓΘ
Ή‘Έ“Ιζœ÷¥ζ”οΈΡΩΈ≥ΧΒ°…ζ“‘ά¥Θ§≥–‘Ί”οΈΡΩΈ≥ΧΡΎ»ίΒΡ÷ς“Σ «ΈΡ―Γ–ΆΒΡ”οΈΡΫΧ≤ΡΓΘ”οΈΡΫΧ―ßΡΎ»ί÷ς“Σ «Ά®ΙΐΫΧ ΠΕ‘―Γ»κΫΧ≤ΡΒΡ“ΜΤΣΤΣΩΈΈΡΒΡΫβΕΝΕχ―Γ‘ώ≥ œ÷≥ωά¥ΒΡΓΘ“ρ¥ΥΘ§ΉΦ»ΖΑ―Έ’ΈΡΧεΒΡΚ§“εΓΔ…ν»κάμΫβ Ε±πΈΡΧεΕ‘”οΈΡΕΝ–¥ΫΧ―ßΒΡ“β“εΘ§÷±Ϋ”ΙΊœΒ”οΈΡΫΧ―ßΡΎ»ίΒΡ―Γ‘ώΓΔ»ΖΕ®ΚΆ≥ œ÷Θ§ΡΥ÷Ν”οΈΡΫΧ―ßΡΩ±ξΒΡ¥ο≥…ΓΘ
ΈΡΧε «÷ΗΨΏ”–ΡΎ»ί–Έ ΫΒΡΙ≤Ά§ΧΊ’ςΘ§”…ΈΡ’¬ΜρΈΡ±ΨœΒΆ≥Ης“ΣΥΊ”–ΜζΫαΚœΕχ≥ œ÷ΒΡ’ϊΧεΉ¥Ο≤Θ§≤ΔΨΏ”–œύΥΤΙΠΡήΒΡΈΡ±Ψάύ–ΆΓΘΈΡΧε”–÷÷÷÷≤ΜΆ§ΒΡ≥ΤΈΫΘ§»γΈΡ’¬Χε≤ΟΓΔΈΡ’¬―υ ΫΓΔΈΡ’¬Χε ΫΓΔΈΡ±ΨΧε ΫΒ»ΓΘ‘ΎΙΐ»ΞΘ§»ΥΟ«Τ’±ιΑ―ΈΡΧεΩ¥ΉςΈΡ’¬ΜρΈΡ±ΨΒΡ–Έ ΫΖΕ≥κΘ§‘Ύ”οΈΡΫΧ―ß ΒΦυ≤ψΟφ”÷ΫΪΫΧ―ßΈΡΧεΜλΆ§’φ ΒΕΝ–¥ΒΡΈΡΧεΘ§“‘÷¬‘Ύάμ¬έΚΆ ΒΦυ÷–≥ωœ÷≤Μ…ΌΈσ«χΓΘ‘Ύ¥ΥΘ§Έ“Ο«ΧΊ±π«ΩΒςΘΚΈΡΧε≤ΜΫω «–Έ ΫΘ§“≤ «ΡΎ»ίΚΆΙΠΡήΘ§ «–Έ ΫΓΔΡΎ»ίΚΆΙΠΡήΒΡΫαΚœΧεΓΘΈΡΧεΦ» «Ρ≥“ΜάύΈΡ’¬ΜρΈΡ±ΨΒΡΡΎ»ίΓΔ–Έ ΫΚΆΙΠΡήΒΡœύΆ§ΜρœύΥΤΧΊ’ςΒΡ≥ιœσΗ≈ά®Θ§“≤ «≥ιœσΈΡ’¬Η≈ΡνΒΡΨΏΧεΜ·ΓΘ‘Ύ”οΈΡΫΧ―ß ΒΦυ÷–Θ§Έ“Ο«÷°Υυ“‘«ΩΒς“άΨίΈΡΧε»ΖΕ®ΫΧ―ßΡΎ»ίΘ§ «“ρΈΣΘΚ
ΒΎ“ΜΘ§÷Μ”– ΕΤδΧεΘ§≤≈Ρή÷ΣΤδ“εΓΘΓΑΧεΓ±÷ΗΒΡ «ΈΡ±ΨΧε ΫΘ§ΓΑ“εΓ±÷ΗΒΡ «œύΕ‘”Ύ–Έ ΫΕχ”÷≤ΜΡήΆ―άκ–Έ ΫΒΡ τ”ΎΡΎ»ίΖΕ≥κΒΡ“βΥΦΓΔ“β“εΓΔ“βΈΕΓΔ“εάμΓΔ÷Φ“βΒ»ΓΘΫβΕΝΈΡ±ΨΘ§÷Μ”–œ»ΝΥΫβΈΡΧε τ–‘Θ§≤≈Ρή’ΐ»ΖΝλΜαΚΆΑ―Έ’ΤδΧΊΕ®ΡΎ»ίΓΘ»γΟϊΝΣΓΑ÷–ΜΣΟώΙζΆρΥξΘ§‘§ άΩ≠«ßΙ≈Γ±Θ§ΦΌ»γΈ“Ο«≤Μ ΕΕ‘ΝΣ÷°ΧεΘ§Μρ’ΏΥΒ’βΗ±Ε‘ΝΣ≤Μ «Α¥Ε‘ΝΣΒΡ––ΩνΗώ Ϋ ι–¥ΚΆ’≈ΧυΒΡΘ§Έ“Ο«ΨΆΕΝ≤Μ≥ωΓΑ‘§ άΩ≠Ε‘≤ΜΤπ÷–ΜΣΟώΙζΓ±ΒΡΖμ¥Χ“βΈΕΓΘΈΡ―ß «”Ο–ΈœσΖ¥”≥…ζΜνΘ§ΈΡ―ßΈΡ±Ψ¥φ‘ΎΉ≈Ω’ΑΉΚΆΈ¥Ε®ΒψΘ§ΉςΦ“ΒΡ–¥Ής“βΆΦ”κΈΡ±Ψ≥ œ÷ΒΡ“β“εΓΔΕΝ’ΏΒΡΫ” ήάμΫβ≥Θ≥Θ≥ωœ÷≤Μ“Μ÷¬ΒΡ«ιΩωΘ§’β «ΈΡ―ß…ζ≤ζΚΆ¥Ϊ≤ΞΙΐ≥Χ÷–ΦΪ’ΐ≥ΘΒΡœ÷œσΓΘ“ρ¥ΥΘ§Έ“Ο«ΫβΕΝΈΡ―ßΉςΤΖΘ§ΚήΕύ ±ΚρΩ…“‘Φϊ» Φϊ÷«Θ§‘ –μΓΑ“Μ«ßΗωΕΝ’Ώ”–“Μ«ßΗωΙΰΡΖάΉΧΊΓΘΓ±≤ΜΒΞ“ΣάμΫβ±μ≤ψ“εΘ§ΜΙ“ΣΖΔΨρ…ν≤ψ“εΘΜ≤ΜΒΞ“ΣΕΝΕ°―‘ΡΎ“εΘ§ΜΙ“ΣΕΝ≥ω―‘Άβ“εΓΘΖ«ΈΡ―ßΉςΤΖ”»Τδ «»’≥Θ”Π”ΟΈΡΚΆΙΪΈΡΒΡ–¥ΉςΚΆ¥Ϊ≤ΞΘ§÷ς“Σ «ΈΣΝΥ Β”ΟΓΘ’βΨΆ“Σ«σΉς’ΏΒΡ–¥Ής“βΆΦΓΔΈΡ±Ψ≥ œ÷ΒΡ“β“εΚΆΕΝ’ΏΒΡΫ” ήάμΫβ±Θ≥÷ΗΏΕ»“Μ÷¬Θ§Ψω≤Μ‘ –μΈΡ±Ψ”–Ω’ΑΉΚΆΈ¥Ε®ΒψΓΘΨΆΕΝ’ΏΒΡΫ” ήΕχ―‘Θ§÷ΜΡήΕΔΉΓΈΡ±ΨΒΡ±μ≤ψ“εΚΆ―‘ΡΎ“εΘ§ΕχΨω≤Μ‘ –μ‘Ύ±μ≤ψ“εΚΆ―‘ΡΎ“ε÷°Άβ‘Ό»ΞΝΣœκΚΆΧμΦ”Εύ”ύΒΡ“β“εΓΘΆ§ «ΓΑ¬δΜ® ±ΫΎΓ±ΓΔΓΑΜΤΚ”÷°Υ°Γ±Θ§ ΪΗηΈΡ±Ψ”κ…ζΈοΫΧΩΤ ιΓΔΒΊάμΫΧΩΤ ιΥυ÷Η≥ΤΒΡ“β“ε≤Δ≤ΜΆξ»ΪœύΆ§ΓΘΕ‘¥ΥΘ§EΘ°DΘ°Κ’œΘ‘Ύ≤ϊ ΆΫβΕΝΈΡ±ΨΒΡΖΕ–ΆΚœ –‘±ξΉΦ ±Χα–―Έ“Ο«ΘΚΓΑ»γΙϊ“ΜΗωΈΡ±Ψ «Α¥ΩΤ―ß¬έΈΡΒΡΖΫ Ϋ–¥≥…ΒΡΘ§Ρ«Ο¥Θ§”ΎΤδ÷–Ϋ“ Ψ≥ωΡ≥÷÷”Α…δ“εΨΆ «≤ΜΚœ ΒΡΓΘΓ±[1]Θ®p490 Ω…“‘’βΟ¥ΥΒΘ§ΈΡ±ΨΧε Ϋ«±‘ΎΒΊΙφΕ®Έ“Ο«”ΠΗΟΕΝ ≤Ο¥ΚΆ‘θ―υΕΝΘ§≤ΜΆ§Χε ΫΈΡ±ΨΒΡΡΎ»ίΫβΕΝ¬Ζ ΐ «≤ΜΆξ»ΪœύΆ§ΒΡΓΘ”οΈΡΫΧ”ΐΒΡ“ΜΗω÷Ί“ΣΡΩ±ξΨΆ «≈ύ―χ―ß…ζ’ΐ»ΖάμΫβΚΆ‘Υ”ΟΉφΙζ”ο―‘ΈΡΉ÷ΒΡΡήΝΠΓΘ»γΙϊ≤Μ“‘ΈΡ±ΨΧε ΫΉςΈΣ»ΖΕ®”οΈΡΫΧ―ßΡΎ»ίΒΡ“άΨίΘ§ΫΧ ΠΡήΑο÷ζ―ß…ζ’ΐ»ΖΒΊάμΫβΩΈΈΡΒΡ“βΥΦ¬πΘΩ–λΈΡΤλ÷Ρœ ΟςΒΊΖ¥Ε‘ΓΑΑ¥’’ ΪΗηΒΡΖΫ Ϋ»Ξ‘ΡΕΝ ΪΗηΘ§Α¥’’–ΓΥΒΒΡΖΫ Ϋ»Ξ‘ΡΕΝ–ΓΥΒΘ§Α¥ΈΡ―ß–ά…ΆΒΡΖΫ Ϋ»Ξ‘ΡΕΝΈΡ―ßΉςΤΖ»»ñΓΘ‘Ύ¥ΥΘ§Έ“Ο«≤ΜΫϊ“ΣΈ ΘΚΡ―ΒάΡήΑ¥‘ΡΕΝΩΤ―ßΥΒΟςΈΡΒΡΖΫ Ϋά¥ΕΝ ΪΗη¬πΘΩΥΒΨΏΧε“ΜΒψΘ§Έ“Ο«ΡήΑ¥ΕΝ“ΜΑψΥΒΟς ιΒΡΖΫ Ϋά¥ΕΝΓΑΑΉΖΔ»ΐ«ß’…Θ§‘Β≥νΥΤΗω≥ΛΓ±ΓΔΓΑΗΏΧΟΟςΨΒ±·ΑΉΖΔΘ§≥·»γ«ύΥΩΡΚ≥…―©Γ±¬πΘΩ≤ΜΫω’β―υ≤Μ––Θ§ΨΆ «Α¥…ΔΈΡΒΡΖΫ Ϋά¥‘ΡΕΝ“≤≤Μ––ΓΘΦ¥ Ι «–λΈΡΝ–ΨΌΒΡ–ΓΥΒΓΔ¥ΪΦ«ΓΔ±®ΗφΈΡ―ßΓΔ…ΔΈΡΒ»–¥»ΥΉςΤΖΒΡΡΎ»ίΫβΕΝ¬Ζ ΐ“≤≤ΜΆξ»ΪœύΆ§Θ§Έ“Ο«Ήή≤ΜΡήΑ¥‘ΡΕΝ–ΓΥΒΒΡΖΫ Ϋά¥ΕΝ–¬Έ≈ΚΆ¥ΪΦ«ΓΘ“ρΈΣ–ΓΥΒ”κ–¬Έ≈ΓΔ¥ΪΦ«Υυ–π–¥ΒΡ»ΥΚΆ ¬≤Δ≤Μ «“ΜΜΊ ¬ΓΘΈ“Ο«’φ≈Σ≤ΜΟςΑΉΘ§–λΈΡΨΙΗ“Χτ’Ϋ”οΈΡ‘ΡΕΝΫΧ―ßΒΡ’β“ΜΉνΜυ±ΨΒΡ≥Θ ΕΘΩ
ΒΎΕΰΘ§÷Μ”– ΕΤδΧεΘ§≤≈ΡήœΰΤδ”ΟΓΘΈΡΧε « ”Π ±¥ζΒΡΖΔ’Ι±δΜ·ΚΆ…γΜαΫΜΆυΒΡ–η“ΣΕχ≤ζ…ζΒΡΓΘ”–”Ο±Ί”–ΧεΘ§ΈόΧε±ΊΈό”ΟΘ§Χε”Ο≤ΜΩ…Ζ÷ΓΘΧΊΕ®ΒΡΡΎ»ίΓΔΧΊΕ®ΒΡ–¥Ής“βΆΦ―Γ‘ώΧΊΕ®ΒΡΈΡΧεΘ§ΧΊΕ®ΒΡΈΡΧε±μœ÷ΧΊΕ®ΒΡΡΎ»ίΘ§ Βœ÷ΈΡ±ΨΧΊΕ®ΒΡΙΠΡήΓΘΈΡ―ßΈΡΧεΤΪ”Ύ…σΟάΘ§¥”ΕΝ’ΏΫ” ήΒΡΫ«Ε»Ω¥Θ§÷Ί‘Ύ―§Χ’ΓΔΗ–»ΨΚΆΝλΈρΘΜΕχ ”ϸΡΧεΤΪ”Ύ Β”ΟΘ§¥”ΕΝ’ΏΫ” ήΫ«Ε»Ω¥Θ§÷Ί‘Ύ»œ÷ΣΚΆ––Ε·ΓΘΧ»»τ≤Μ ΕΤδΧεΘ§Ε‘”οΈΡ‘ΡΕΝΫΧ―ßά¥ΥΒΘ§Έ“Ο«ΨΆ≤ΜΩ…Ρή÷ΣΒάΈΣ ≤Ο¥ΕΝΚΆΕΝ ≤Ο¥Θ§“≤ΨΆ≤ΜΡή’ΐ»ΖΑ―Έ’ΈΡ±ΨΡΎ»ίΚΆΉΦ»ΖάμΫβΉς’ΏΒΡ–¥Ής“βΆΦΓΘ”οΈΡ‘ΡΕΝΫΧ―ßΘ§ Β÷ …œΨΆ «‘ΎΈΡΧε“β ΕΒςΩΊœ¬ΒΡ“Μ÷÷‘ΡΕΝ––ΈΣΓΘΟΜ”–ΈΡΧε“β ΕΒΡ≤Έ”κΚΆΒςΩΊΒΡ‘ΡΕΝΘ§ΨΆ «ΒΆ–ß…θ÷ΝΈό–ßΒΡ‘ΡΕΝΓΘ”οΈΡ–¥ΉςΫΧ―ßΘ§ Β÷ …œΨΆ «‘ΎΨΏΧε”οΨ≥÷–ΒΡΈΡΧεΥΦΈ§ΫΧ―ßΓΘΟΜ”–”οΨ≥“β ΕΚΆΈΡΧεΥΦΈ§ΒΡΒςΩΊΘ§ΨΆ «ΒΆ–ß…θ÷ΝΈό–ßΒΡ–¥ΉςΫΧ―ßΓΘΒ±»ΜΘ§―ß…ζΈΡΧε“β ΕΒΡ≈ύ―χ≤ΜΩ…“ΜθμΕχΨΆΘ§“ΣΨ≠άζ¥”ΈόΒΫ”–ΓΔ”……ΌΒΫΕύΓΔ¥”≤ΜΉ‘ΨθΒΫΉ‘ΨθΒΡΙΐ≥ΧΘ§±Ί–κΉώ―≠―ß…ζ»œ÷ΣΖΔ’ΙΒΡΙφ¬…ΚΆ”οΈΡΫΧ”ΐΫΧ―ßΒΡΙφ¬…Θ§ΒΪΈ“Ο«≤ΜΡή¥” Φ÷Ν÷’ΫΪΈΡΧε“β ΕΨή”Ύ”οΈΡΫΧ―ßΟ≈ΆβΓΘ«ΑΈΡ“― ωΘ§”οΈΡΫΧ”ΐΒΡ“ΜΗω÷Ί“ΣΡΩ±ξΨΆ «≈ύ―χ―ß…ζ’ΐ»ΖάμΫβΚΆ‘Υ”ΟΉφΙζ”ο―‘ΈΡΉ÷ΒΡΡήΝΠΓΘΈΣ¥ο¥ΥΡΩΒΡΘ§ΨΆ±Ί–κΫη÷ζΩΈΈΡ»Ο―ß…ζάμΫβΉς’Ώ «»γΚΈ―Γ‘ώΧΊΕ®Χε Ϋ±μ¥οΧΊΕ®ΡΎ»ί“‘ Βœ÷ΤδΧΊΕ®“βΆΦΒΡΓΘ ‘Έ Θ§Έ“Ο«ΡήΤ≤ΩΣΩΈΈΡΒΡΧε Ϋά¥≥ιœσΧΗ¬έΩΈΈΡΒΡΡΎ»ίΚΆΉς’ΏΒΡ“βΆΦ¬πΘΩ»γΙϊ»±ΖΠΈΡΧε“β ΕΘ§Έ“Ο«ΡήΆ®Ιΐ‘ΡΕΝΚΆ–¥Ής Βœ÷”––ßΒΡ…γΜαΫΜΆυ¬πΘΩ
ΒΎ»ΐΘ§÷Μ”– ΕΤδΧεΘ§≤≈ΡήΒΟΤδΖ®ΓΘ’βάοΒΡΓΑΖ®Γ±Θ§÷ς“Σ «÷ΗΆ®ΙΐΕ‘“ΜΤΣΤΣΨΏΧεΩΈΈΡΒΡΫΧ―ßΕχ»Ο―ß…ζάμΫβΚΆ’ΤΈ’≤Δ”–Ω…Ρή‘Υ”Ο”Ύ–¥Ής ΒΦυΒΡ»Γ≤ΡΖΫΖ®ΓΔΙΙΥΦΖΫΖ®ΓΔ±μœ÷ΖΫΖ®ΦΑΦΦ«…Β»ΓΘΈ“Ο«÷ΣΒάΘ§“βœσ « ΪΗηΒΡΜυ±ΨΫ®÷ΰ≤ΡΝœΘ§ΩΆΙέΈοœσ‘Ύ Ϊ»Υ«ιΗ–÷ςΒΦœ¬ΜαΖΔ…ζ―œ÷Ί±δ“λΘ§œώΓΑΑΉΖΔ»ΐ«ß’…Θ§‘Β≥νΥΤΗω≥ΛΓ±ΓΔΓΑ ÷ΉΞΜΤ…œΈ“≤ΜΖ≈Θ§ΫτΫτΧυ‘Ύ–ΡΈ―…œΓ±–¥»κ ΪΗηΘ§ΥδΖ¥≥ΘΒΪΚœ«ιΘ§ΨΓΙήΩδ’≈ΒΪ»Ο»ΥΗ–ΒΫ≤Μ «‘ΎΩδ’≈ΓΘΧ»»τ’β―υ–¥…ΔΈΡΘ§ΨΆΜα»Ο»ΥΗ–ΒΫ”–ψΘ≥Θ«ι≥ΘάμΚΆ≤Μ¬Ή≤ΜάύΝΥΓΘ”…¥ΥΩ¥ά¥Θ§–¥ΉςΖΫΖ®ΚΆΦΦ«…Ήή «¥φ‘ΎΨΏΧεΒΡΈΡ±ΨΧε Ϋ÷–Θ§άκΩΣΝΥΨΏΧεΒΡΈΡΧεΘ§Έ“Ο«ΨΆΚήΡ―Τά≈–Ρ≥÷÷–¥ΉςΖΫΖ®ΒΡ’ΐΈσΗΏœ¬”≈Ν”Θ§Ηϋ≤Μ“ΣΥΒ‘Υ”Ο”Ύ–¥Ής ΒΦυΝΥΓΘΨΆ“‘–¥ΉςΒΡΙΙΥΦά¥ΥΒΘ§“ρΈΣΈΡ―ßΈΡΧε÷¬ΝΠ”Ύ”Σ‘λΖαΗΜΒΡ“β‘ΧΘ§ΫαΙΙΡΘ Ϋ‘ΎΉώ―≠ΓΑ¥σΧε–κ”–Γ±ΒΡ«ΑΧαœ¬Ήή ««σ–¬«σ±δΘ§“ρΕχΉή « Ι”ΟΡφœρΥΦΈ§ΓΔ«σ“λΥΦΈ§ΒΡΙΙΥΦΖΫΖ®ΓΘΕχ ”ϸΡΧεΘ§÷ς“Σ «”Π”ΟΈΡΘ§”…”ΎΥϋΡΎ»ίΦ·÷–ΒΞ“ΜΘ§ΫαΙΙΡΘ ΫΙΧΕ®Θ§”ΟΆΨΒΞ“ΜΘ§“ρΕχ‘ΎΙΙΥΦ…œ≥Θ≥Θ Ι”Ο«σΆ§ΥΦΈ§Μρ’ΐœρΥΦΈ§ΒΡΖΫΖ®ΓΘΤδΥϋœώ–ιΙΙΓΔΩδ’≈ΒΡ–¥Ής ÷Ζ®Θ§œώδ÷»ΨΓΔΤΧΒφΓΔœσ’ςΓΔΆ®Η–ΓΔ≥ΡΆ–ΓΔ“÷―οΓΔΑΒ ΨΒ»ΨΏΧε–¥ΉςΦΦΖ®÷ΜΡή ”Ο”ΎΈΡ―ßΈΡΧεΘ§Χ»»τ”Ο”Ύ ”ϸΡΧεΒΡ–¥ΉςΘ§Ρ«ΨΆΦ»≤ΜΒΟΧεΘ§“≤≤ΜΚœ”ΟΝΥΓΘΉή÷°Θ§“ΜΕ®ΒΡ–¥ΉςΖΫΖ®ΚΆΦΦ«…Β»Θ§÷ΜΡή¥φ‘Ύ”ΎΨΏΧεΒΡΈΡΧε÷–Θ§Έ“Ο«“≤÷Μ”–Ά®ΙΐΨΏΧεΈΡΧεΒΡΫβΕΝΘ§≤≈Ρή÷ΣΒάΈΡ’¬”ΠΗΟ‘θ―υ–¥Θ§≤ΜΡήΡ«―υ–¥Θ§ΫχΕχΆ®œΰΈΡ’¬ΒΡ–¥Ής÷°ΒάΘ§–¥Ής÷°Ζ®ΓΘ”οΈΡΫΧ―ßΒΡ“ΜΗω÷Ί“ΣΡΩ±ξΨΆ «Ά®Ιΐ‘ΡΕΝ÷Ηœρ–¥ΉςΓΘΕχ“Σ Βœ÷’β“ΜΡΩ±ξΘ§ΨέΫΙ”ΎΈΡ±Ψ‘θΟ¥ΥΒΚΆΈΣ ≤Ο¥’βΟ¥ΥΒΒΡ–¥ΉςΖΫΖ®ΦΑΦΦ«…Θ§Έό“… «÷Ί“ΣΒΡΫΧ―ßΡΎ»ίΘ§ΒΪ’β «“‘ Ε±πΈΡΧεΈΣ«ΑΧαΒΡΓΘΈ“Ο«≥–»œ–λΈΡΥυΥΒΒΡΓΑ≤ΜΆ§ΈΡΧε÷°ΦδΒΡ–¥Ής“’ θ «ΜΞœύΆ®»ΎΒΡΓ±Θ§ΒΪ“≤±Ί–κΩ¥ΒΫΓΑΈΡ±ΨΆ§ΕχΡ©“λΓ±Θ®≤ήΊßΘΚΓΕΒδ¬έ¬έΈΡΓΖΘ©Θ§”–≤Μ…Ό–¥Ής“’ θ « ήΒΫΈΡΧε―œΗώœό÷ΤΒΡΘ§≤Δ≤Μ «Ω…“‘Υφ±ψΆ®»ΎΒΡΓΘΤ©»γΥΒΘ§ΈΡ―ߥ¥ΉςΩ…“‘Έό÷–…ζ”–Θ§ΒΪ–¬Έ≈±®ΒάΓΔΒς≤ι±®ΗφΓΔΩΤ―ß Β―ι±®ΗφΓΔ≤ζΤΖΥΒΟς ιΨΆ≤Μ‘ –μΘΜΩδ’≈‘Ύ ΪΗηάοΩ…“‘»Ο»Υ≤ΜΗ–ΒΫ «Ωδ’≈Θ§ΒΪ‘Ύ…ΔΈΡάοΨΆΜα»Ο»ΥΗ–ΒΫ±π≈ΛΘ§Εχ–¬Έ≈ΓΔ¥ΪΦ«ΓΔΩΤ―ßΥΒΟςΈΡΒ»‘ρ «Ωδ’≈ΒΡΫϊ«χΓΘ
–λΈΡ÷°Υυ“‘ΖώΕ®ΈΡ±ΨΧε Ϋ‘Ύ”οΈΡΫΧ―ß÷–ΒΡΙφΕ®–‘Ής”ΟΘ§“ΜΗω÷Ί“Σ‘≠“ρΨΆ «Ά―άκ”οΈΡΫΧ―ß ΒΦ Θ§≤ΜΝΥΫβ―ß…ζ«ιΩωΘ§Ρ° ””οΈΡΫΧ”ΐΡΩ±ξΓΘΨίΫϋ °Ρξά¥“Μ÷±÷ς≥÷ΚΰΡœ ΓΗΏΩΦΉςΈΡΤάΨμΙΛΉςΒΡ≥¬ΙϊΑ≤ΫΧ ΎΥΒΘΚΗΏΩΦΉςΈΡΒ≠Μ·ΈΡΧεΘ§ΓΑΩΦ…ζΒΡΉςΈΡΖ«ΒΪΟΜ”–≥ωœ÷Έ“Ο«ΥυΤΎ¥ΐΒΡΡ«÷÷Νν»Υ–άœ≤ΒΡœ÷œσΘ§Ζ¥ΒΙΫ–»ΥΒΘ”«Γ≠Γ≠ΚΰΡœ Γ2004Ρξ38ΆρΩΦ…ζΘ§2005Ρξ42ΆρΩΦ…ζΘ§Έ“‘ΎΤάΨμ÷–ΨΙΟΜ”–ΖΔœ÷“ΜΤΣ÷–Ιφ÷–ΨΊΒΡ“ι¬έΈΡΜρΦ«–πΈΡΓΘΓ±[2]± ’Ώ≥ΛΤΎΒΘ»Έ ΠΖΕ‘Κ–Θ÷–ΈΡΉ®“ΒΒΡ–¥ΉςΫΧ―ß»ΈΈώΘ§Ψί≤Μ÷Ι“ΜΫλ“≤≤Μ÷Ι“ΜΗωΗ’»κ―ßΒΡ―ß…ζΖ¥”≥ΘΚΓΑ…œΝΥΗΏ÷–Θ§ΩΦ¥σ―ß≥…ΝΥΈ“Ο«ΒΡΖήΕΖΡΩ±ξΘ§Υυ“‘ΕΦ–¥ΜΑΧβΉςΈΡΓΘ¥”ΗΏ“ΜΒΫΗΏ»ΐΘ§–¥ΝΥΕύ…ΌΗωΜΑΧβΉςΈΡΕΦ ΐ≤Μ«εΘ§ΒΪΈ“Ο«÷ΜΜα–¥“Μ÷÷Χε ΫΒΡΜΑΧβΉςΈΡΘ§ΕχΕ‘ΤδΥϋΧε Ϋ»¥“Μ«œ≤ΜΆ®Θ®“ΐΉ‘± ’Ώ÷¥ΫΧΒΡ÷–ΈΡœΒ2005ΓΔ2007ΓΔ2008ΦΕ―ß…ζ–¥ΉςΡήΝΠΒς≤ι≤ΡΝœΘ©ΓΘΨΓΙή≥ωœ÷’β÷÷Ή¥ΩωΒΡ‘≠“ρ «ΕύΖΫΟφΒΡΘ§ΒΪΈ“Ο«Ήή≤ΜΡήΥΒ”κ≤Μ…ΌΫΧ Π≤ΜΡή“άΨίΈΡ±ΨΧε Ϋ»ΖΕ®”οΈΡΫΧ―ßΡΎ»ίΟΜ”–“ΜΒψΙΊœΒΑ…ΓΘ―ß…ζΆ®ΙΐΫ” ή12ΡξΒΡ”οΈΡΫΧ”ΐΘ§ΗυΨίΉ‘Έ“…ζ¥φΖΔ’ΙΒΡ–η“ΣΚΆ…γΜαΖΔ’ΙΒΡ–η«σΘ§Ρή–¥ΦΗ÷÷ΚœΧε”–”ΟΒΡΈΡ’¬Θ§≤ΜΒΪ≤Μ”Π «“Μ÷÷…ίΆϊΘ§Εχ«“”ΠΗΟ «”οΈΡΫΧ”ΐ»ί“Ή¥οΒΫΒΡΡΩ±ξΓΘΕχ“Σ¥ο≥…’β“ΜΡΩ±ξΘ§ΨΆ±Ί–κ“άΨίΈΡ±ΨΧε Ϋ»ΖΕ®ΫΧ―ßΡΎ»ίΓΘ’ΐ «‘Ύ’βΗω≤ψΟφ…œΘ§Έ“Ο«ΥυάμΫβΚΆ÷ς’≈ΒΡ“άΨίΈΡ±ΨΧε Ϋ»ΖΕ®ΫΧ―ßΡΎ»ίΘ§ΨΆ «Ά®Ιΐ“ΐΒΦ―ß…ζΗ–÷ΣΩΈΈΡΒΡ―‘”ο–Έ Ϋ»ΞάμΫβΩΈΈΡΒΡ―‘”οΡΎ»ίΚΆ“βΆΦΘ§ΫχΕχ’ΤΈ’ΩΈΈΡΒΡ―‘”ο–Έ ΫΘ§÷πΫΞ Βœ÷”…ΕΝΒΫ–¥ΒΡ«®“ΤΘ§“‘ΜώΒΟ‘Υ”Ο”ο―‘ΒΡ±ΨΝλΓΘΤΪάκΈΡ±ΨΧε ΫΘ§≥όΧΗΓΑ―ή…ζΓ±ΓΔΓΑΦ≥»ΓΓ±ΓΔΓΑ‘Υ”ΟΓ±÷°άύΒΡΓΑΫΧ”ΐ÷ΒΓ±Θ§Ε‘≈ύ―χ―ß…ζ ΒΦ ΒΡ”οΈΡΕΝ–¥ΡήΝΠ Β‘ΎΟΜ”–Εύ¥σΦέ÷ΒΓΘ
Εΰ
–λΈΡΜλœΐΝΥΗω»ΥΉ‘ΖΔ‘ΡΕΝΚΆ”οΈΡΩΈΧΟΫΧ―ß‘ΡΕΝΓΔ’ΐ‘Ύ≥…≥ΛΒΡΕΝ’Ώ‘ΡΕΝ”κ≥… λΕΝ’ΏΒΡ‘ΡΕΝΒΡΫγœόΓΘΉςΈΣΗω»ΥΉ‘ΖΔ‘ΡΕΝΘ§“ΜΑψΕΝΒΡ «ΡΎ»ίΘ§ΕΝΒΡ «–Υ»ΛΘ§Εύ ΐ«ιΩωœ¬ «≤ΜΜαΩΦ¬«Ηϋ≤ΜΜα…νΨΩΥυΕΝΒΡΈΡ±ΨΧε ΫΒΡΓΘΕΝ ≤Ο¥ΓΔ‘θ―υΕΝΓΔΕΝ≥ω ≤Ο¥Θ§Ω…“‘ΥΒ «ΓΑΈ“ΒΡ‘ΡΕΝΈ“Ήω÷ςΓ±Θ§“ρΕχΡ―Οβ¥φ‘Ύ“ΜΕ®≥ΧΕ»ΒΡΥφ“β–‘ΚΆΟΛΡΩ–‘ΓΘΕχ”οΈΡΩΈΧΟΒΡ‘ΡΕΝ «”–±»ΫœΟς»ΖΒΡΫΧ―ßΡΩ±ξΒΡΘ§“ρ¥ΥΘ§ΨΆ≤ΜΡή≤ΜΕ‘‘ΡΕΝΒΡΡΎ»ίΚΆΖΫΖ®”–ΥυΙφœόΘ§ΕχΫΧ Π“ΣΉωΒΡΙΛΉς»Ζ ΒΨΆ «ΓΑ―ß…ζ≤Μœ≤ΜΕΒΡΘ§ ΙΥϊœ≤ΜΕΘΜ―ß…ζΕΝ≤ΜΕ°ΒΡΘ§ ΙΥϊΕΝΕ°ΘΜ―ß…ζΕΝ≤ΜΚΟΒΡΘ§ ΙΥϊΕΝΚΟΓ±ΓΘΈΣ¥ΥΘ§ΨΆ±Ί–κ“άΨίΈΡ±ΨΧε Ϋ»ΖΕ®ΫΧ―ßΡΎ»ίΓΘ“ρΈΣΈΡ±ΨΧε ΫΕ‘‘ΡΕΝΒΡΡΎ»ί «”–Υυœό÷ΤΒΡΘ§Ε‘‘ΡΕΝΒΡΖΫΖ® «”–Υυ―Γ‘ώΒΡΓΘΒάάμΚήΦρΒΞΘ§Έ“Ο«Ήή≤ΜΡήΑ―–ΓΥΒΥυ–π–¥ΒΡ»ΥΚΆ ¬Β»Ά§”Ύ–¬Έ≈±®ΒάΒΡ»ΥΚΆ ¬Α…Θ§Ήή≤ΜΡή”Οά ΕΝ ΪΗηΒΡΖΫΖ®ά¥ΕΝ“ΜΖί≤ζΤΖΥΒΟς ιΑ…ΓΘΈ“Ο«≤Δ≤Μ“ΜΗ≈Ζ¥Ε‘–λΈΡ÷ς’≈ΒΡΆ®Ιΐ‘ΡΕΝ Ι―ß…ζ»œ ΕΒΫΓΑ―ή…ζ ≤ϥñΓΔΓΑΦ≥»Γ ≤ϥñΓΔΓΑ‘Υ”Ο ≤ϥñȧΒΪ «Θ§»γΙϊ―ß…ζΕ‘‘ΡΕΝΕ‘œσ≤Μœ≤ΜΕΓΔΕΝ≤ΜΕ°ΓΔΕΝ≤ΜΚΟΘ§”÷ΜΙΡήΓΑ―ή…ζ ≤ϥñΓΔΓΑΦ≥»Γ ≤ϥñΓΔΓΑ‘Υ”Ο ≤ϥñΘΩΩ…“‘’βΟ¥ΥΒΘ§ Ι―ß…ζœ≤ΜΕΓΔΕΝΕ°ΓΔΕΝΚΟ «”οΈΡ‘ΡΕΝΫΧ―ßΒΡ«ΑΧαΚΆΜυ¥ΓΓΘάκΩΣΝΥ’βΗω«ΑΧαΚΆΜυ¥ΓΘ§ΥΒ ≤Ο¥ΓΑ―ή…ζΓ±ΓΔΓΑΦ≥»ΓΓ±ΓΔΓΑ‘Υ”ΟΓ±Θ§ΕΦ «…ίΧΗΓΘ
÷ΎΥυ÷ή÷ΣΘ§≥… λΜράμœκΕΝ’ΏΒΡ‘ΡΕΝ”κ’ΐ‘Ύ≥…≥Λ÷–ΒΡΕΝ’ΏΒΡ‘ΡΕΝ «”–ΗΏœ¬”≈Ν”÷°±πΒΡΓΘ≥… λΕΝ’ΏΤΨΉ≈Ε‘ΈΡΧεΒΡ λοΰΘ§“―Ψ≠–Έ≥…ΝΥΩλΫίΉΦ»ΖΒΡ‘ΡΕΝΖ¥”ΠΡήΝΠΓΘ“ΜΑψΥΒά¥Θ§≥… λΕΝ’ΏΡΟΒΫ–ΓΥΒ≤ΜΜαΒ±–¬Έ≈ΓΔ¥ΪΦ«ΕΝΘ§ΦϊΒΫΙΪΈΡ≤ΜΜαΒ±Ή≈Ϋ÷…œ’≈ΧυΒΡΙψΗφΕΝΓΘΒΪ «Θ§’ΐ‘Ύ≥…≥Λ÷–ΒΡΕύ ΐΕΝ’Ώ «≤ΜΜα”–’β÷÷Φχ±πΖ¥”ΠΡήΝΠΒΡΓΘ”οΈΡΫΧ―ß“ΣΑ―’ΐ‘Ύ≥…≥Λ÷–ΒΡΕΝ’Ώ≈ύ―χ≥…±»ΫœάμœκΒΡΕΝ’ΏΘ§ΨΆ±Ί–κ“άΨίΈΡ±ΨΧε Ϋ―Γ‘ώΫΧ―ßΡΎ»ίΘ§ΨΆ «“ΣΓΑΑ¥’’ ΪΗηΒΡΖΫ Ϋ»Ξ‘ΡΕΝ ΪΗηΘ§Α¥’’–ΓΥΒΒΡΖΫ Ϋ»Ξ‘ΡΕΝ–ΓΥΒΘ§Α¥ΈΡ―ß–ά…ΆΒΡΖΫ Ϋ»Ξ‘ΡΕΝΈΡ―ßΉςΤΖΓ±ΓΘΈ“Ο«ΚΆ–λΫ≠œ»…ζ“Μ―υΘ§Ε‘Β±œ¬”οΈΡΫΧ―ßΒΡΦ®–ß“≤ «≤Μ¬ζ“βΒΡΓΘ“ΜΗωΈψ”ΙΜδ―‘ΒΡ ¬ Β «ΘΚΕύ ΐ―ß…ζ¥”–Γ―ß÷–ΗΏΡξΦΕΤπΘ§ΦΗΚθΟΩΗω―ßΤΎΕΦ“Σ―ßœΑ ΪΗηΓΔ…ΔΈΡΓΔ–ΓΥΒΒ»Θ§ΒΪΒΫΗΏ÷–±œ“ΒΘ§ΡήΕΝ“ΜΑψ ΪΗηΓΔ…ΔΈΡΓΔ–ΓΥΒΒΡ―ß…ζΩ…Ρή≤Μ «ΚήΕύΓΘ±±Ψ©¥σ―ß÷–ΈΡœΒΫΧ ΎΈ¬»εΟτΥΒ¥σ―ßΩΣ…η¥σ―ß”οΈΡΩΈΒΡ÷ς“ΣΉς”ΟΨΆ «Α――ß…ζ±Μ”Π ‘ΫΧ”ΐΓΑΑήΜΒΓ±ΝΥΒΡ”οΈΡΈΗΩΎΗχ÷Ί–¬Βς ‘Ιΐά¥ΓΘ―ß…ζΒΡ”οΈΡΈΗΩΎ±ΜΓΑΑήΜΒΓ±Θ§ΨΓΙή‘≠“ρΚήΕύΘ§ΒΪΤδ÷–“ΜΗω÷Ί“Σ‘≠“ρΨΆ «‘Ύ”οΈΡΫΧ―ß ΒΦυ÷–Θ§œύΒ±“Μ≤ΩΖ÷”οΈΡΫΧ Π»±ΖΠΓΑ“άΨίΈΡ±ΨΧε Ϋ»ΖΕ®ΫΧ―ßΡΎ»ίΓ±ΒΡΉνΜυ±Ψ÷Σ ΕΚΆ”Π”–ΒΡΉ‘Ψθ“β ΕΓΘΡ≥–Γ―ß”οΈΡΫΧ ΠΒΡ“ΜΧΟΙΪΩΣΩΈΘ§ΩΈΧβ «‘Δ―‘Ι ¬ΓΕΈΎ―ΜΚΆΚϋάξΓΖΘ§‘ΎΫΧ―ßΙΐ≥Χ÷–Θ§”–―ß…ζ≤ΜΫβΒΊΈ ΘΚΓΑάœ ΠΘ§Έ“Ω¥≤ΜΩ…ΡήΑ…Θ§ΈΎ―ΜΟΜΡ«Ο¥…ΒΑ…Θ§‘θΟ¥Μα…œΚϋάξΒΡΒ±ΡΊΘΩΈ“Ο«“ΜΡξΦΕ―ßΙΐΒΡΓΕΈΎ―ΜΚ»Υ°ΓΖΘ§ΈΎ―Μ≤Μ «ΆΠ¥œΟςΒΡ¬πΘΩΓ±’βΈΜΫΧ Π“ρ“Μ ±≤ΜΡήΫβ¥πΘ§Ρ’–Ώ≥…≈≠ΒΊΚ«≥β―ß…ζΒάΘΚΓΑ±’…œΡψΒΡΈΎ―ΜΉλΘΓΓ±’βΈΜΫΧ ΠΟφΕ‘―ß…ζΒΡΧαΈ ÷°Υυ“‘Ζ¥”Π≥ωΗώΘ§¥μΙΐΝΥ”κ―ß…ζΕ‘ΜΑΓΔœρ―ß…ζ Ύ÷ΣΒΡΜζΜαΘ§ΨΆ‘Ύ”ΎΥϊ≤Μ Ε‘Δ―‘÷°ΧεΓΘΦΌ»τ’βΈΜΫΧ Π‘Ύ±ΗΩΈΜΖΫΎΡή”–ΓΑ“άΨίΈΡ±ΨΧε Ϋ»ΖΕ®ΫΧ―ßΡΎ»ίΓ±ΒΡΉνΜυ±Ψ÷Σ ΕΚΆ”Π”–ΒΡΉ‘Ψθ“β ΕΘ§≤ΜΑ―ΈΡ±ΨΧε Ϋ ”ΈΣΓΑ“ΜΗω¥Έ“ΣΒΡ±ΗΩΈΥΦΈ§‘ΣΥΊΓ±Θ§Ρ«Ο¥‘ΎΩΈΧΟ…œ≤ΜΒΞ≤ΜΜα≥ωœ÷”–Υπ Π±μΒΡ≥ωΗώΖ¥”ΠΘ§ΜΙΜα‘Ύ―ß…ζΉν–η“ΣΕ‘ΜΑΉν–η“Σ Ύ÷ΣΒΡ ±ΚρΡήΦΑ ±Ε‘ΜΑœύΜζ Ύ÷ΣΘ§“‘ Βœ÷ΫΧ―ßΡΎ»ίΒΡ…ζ≥…ΓΘΈόΕά”–≈ΦΘ§Ρ≥–¬ΩΈ±ξ”οΈΡΫΧ≤ΡΒΡΓΕ”όΙΪ“Τ…ΫΓΖ“ΜΈΡΒΡΓΑΩΈ«ΑΧα ΨΓ±ΚΆΓΑ―–Χ÷”κΝΖœΑΓ±ΕΦΖ÷±π“Σ―ß…ζΥΦΩΦΧ÷¬έΓΑ”όΙΪ”κ»ΪΦ“»ΥΓ°±œΝΠΤΫœ’Γ· «¥œΟςΒΡΨΌ¥κΘ§ΜΙ «”ό¥άΒΡ––ΈΣΘΩΓ±ΤδΓΕΫΧ ΠΫΧ―ß”Ο ιΓΖΥΒ’βΤΣΩΈΈΡΖ¥”≥ΝΥΈ“ΙζΙ≈¥ζάΆΕ·»ΥΟώΗΡ‘λΉ‘»ΜΒΡΈΑ¥σΤχΤ«ΚΆΦα«Ω“ψΝΠΓΘΫΧ≤Ρ±ύ’Ώ÷°Υυ“‘…η÷ΟΈ±Έ ΧβΚΆΈσΕΝΩΈΈΡΘ§ΨΆ «Α―‘Δ―‘Β±Ής–¥’φΦ« ΒΒΡάζ ΖΈΡœΉΘ§≤ΜΝΥΫβ‘Δ―‘–ιΡβ–‘ΓΔΖμ”ς–‘ΚΆ»Α ά–‘ΒΡΧΊΒψΓΘ»γΙϊ”οΈΡΫΧ Π»±ΖΠΓΑ“άΨίΈΡ±ΨΧε Ϋ»ΖΕ®ΫΧ―ßΡΎ»ίΓ±ΒΡΜυ±Ψ÷Σ ΕΚΆΉ‘Ψθ“β ΕΘ§…ζ”≤ΒΊΑ―ΫΧ≤ΡΫΧ≤ΈΡΎ»ίΑαΫχ”οΈΡΩΈΧΟΘ§––¬πΘΩ–λΫ≠œ»…ζΉή «ΒΘ–Ρ»γΙϊΑ―ΈΡ±ΨΧε ΫΓΑΧα…ΐΒΫΝΥ≤Μ”Π”–ΒΡΒΊΈΜΓ±Θ§ΓΑΜα ΙΫβΕΝΥΦΈ§Ιΐ”Ύ’≠Μ·ΓΔœΗΜ·ΡΥ÷ΝΉ®“ΒΜ·Θ§…θ÷ΝΉΏœρΙ≈ΑεΓΔΫ©Μ·Γ±Θ§ΕχΈ“Ο«‘ρ«Γ«ΓœύΖ¥Θ§»γΙϊ≤ΜΑ―ΈΡ±ΨΧε ΫΉςΈΣ»ΖΕ®ΫΧ―ßΡΎ»ίΒΡ“άΨί÷°“ΜΘ§ΫΪΜα ΙΫβΕΝΥΦΈ§Ιΐ”ΎΖΚΜ·ΓΔ¥÷«≥Μ·ΡΥ÷ΝΖ«”οΈΡΜ·Θ§…θ÷ΝΉΏœρ¬ΰΈό±ΏΦ ΒΡΩ’ΝιΚΆΟΛΡΩΜ·ΓΘ’Ψ‘Ύ”οΈΡΫΧ”ΐΒΡΝΔ≥Γ…œΘ§Έ“Ο« Φ÷’»œΈΣΘΚ”οΈΡΫΧ―ß“ΣΑ―’ΐ‘Ύ≥…≥Λ÷–ΒΡΕΝ’Ώ≈ύ―χ≥…±»ΫœάμœκΒΡΕΝ’ΏΘ§ Ι―ß…ζΨΏ”–’ΐ»ΖάμΫβΚΆ‘Υ”ΟΉφΙζ”ο―‘ΈΡΉ÷ΒΡΡήΝΠΘ§ΨΆ±Ί–κΚΝ≤ΜΕ·“ΓΒΡΦα≥÷ΓΑ“άΨίΈΡ±ΨΧε Ϋ»ΖΕ®ΫΧ―ßΡΎ»ίΓ±ΒΡ‘≠‘ρΓΘΕχΨω≤ΜΡήœώ–λΫ≠œ»…ζΡ«―υΘ§Ήή «“‘Ή®“ΒΕΝ’ΏΜράμœκΕΝ’ΏΒΡ±ξΉΦΩΝ«σ’ΐ‘Ύ≥…≥Λ÷–ΒΡΕΝ’ΏΘ§Κω ”Β±œ¬”οΈΡΫΧ―ß±»ΫœΤ’±ι¥φ‘ΎΒΡΚω¬‘ΈΡΧε’β“ΜΫτΤ»ΒΡœ÷ ΒΈ ΧβΘ§ΈΞΖ¥”οΈΡΫΧ”ΐΫΧ―ßΙφ¬…Θ§ΫωΤΨΗω»ΥΒΡΑ°ΚΟΓΔ–Υ»ΛΓΔ»»«ι»ΞΉΖ«σ≤Μ«– ΒΦ ΒΡΩγ‘Ϋ ΫΖΔ’ΙΓΘ
–λΈΡΜΙΜλœΐΝΥ”οΈΡΫΧ―ßœΒΆ≥÷–ΫΧ ΠœΒΆ≥÷Σ Ε”κ―ß…ζœΒΆ≥÷Σ ΕΒΡΫγœόΓΘœύΕ‘”ΎΨΏΧεΩ…Η–ΒΡΩΈΈΡΘ§ΈΡ±ΨΧε Ϋ±œΨΙ «≥ιœσΗ≈ά®ΒΡ”οΈΡ÷Σ ΕΓΘΕ‘―ß…ζΕχ―‘Θ§Ω…“‘‘ί ±≤Μ÷ΣΜρ÷πΫΞ”–Υυ÷ΣΘ§Φ¥ Ι“Σ«σ―ß…ζ”Π÷ΣΘ§ΆΘΝτ‘Ύ”οΗ–Ή¥Χ§“≤ΈόΖΝΓΘΒΪΕ‘ΫΧ ΠΕχ―‘Θ§ΨΆ≤ΜΡή“ΜΈόΥυ÷ΣΘ§Φ¥ Ι”–Υυ÷Σ“≤≤ΜΡήΉή «ΆΘΝτ‘Ύ”οΗ–Ή¥Χ§Θ§ΜΙ±Ί–κΫχ»κ”ο ΕΉ¥Χ§ΓΘΩΈΧΟΫΧ―ßΦ¥ Ι≤Μ÷±Ϋ”≥ œ÷ΈΡ±ΨΧε Ϋ÷Σ ΕΘ§“≤”Π≥…ΈΣΫΧ ΠΒΡ«±Χ®¥ ΓΘœώ«ΑΈΡΧαΒΫΒΡΡ≥ΫΧ ΠΫΧ―ßΓΕΈΎ―Μ”κΚϋάξΓΖΙΐ≥Χ÷–ΒΡ≥ωΗώΖ¥”ΠΘ§ΨΆ «“ρΈΣ»±ΖΠ‘Δ―‘ΈΡΧε÷Σ ΕΒΡ«±Χ®¥ ΓΘ“≈ΚΕΒΡ «Θ§ΈΡ±ΨΧε ΫΨΙ±Μ–λΈΡ ”ΈΣΩ…”–Ω…ΈόΒΡΓΑ“ΜΗω¥Έ“ΣΒΡ±ΗΩΈΥΦΈ§‘ΣΥΊΓ±ΓΘΩ…“‘’βΟ¥ΥΒΘ§»γΙϊ”οΈΡΫΧ Π«α–≈ΓΔΤΪ–≈–λΈΡΒΡΆαάμ–ΑΥΒΘ§ «ΕœΕœΫΧ≤ΜΚΟ”οΈΡΒΡΓΘΥΒΈσ»ΥΉ”ΒήΘ§“≤≤ΜΈΣΙΐΓΘ
»ΐ
–λΈΡΜλœΐΝΥ”οΈΡΩΈΆ§ΤδΥϋΩΈ≥ΧΒΡΫγœόΓΘΉ‘”οΈΡΕάΝΔ…ηΩΤ“‘ά¥Θ§”οΈΡ÷Μ «―ß–ΘΫΧ”ΐ…η÷ΟΒΡ °ΦΗΟ≈ΩΈ≥Χ÷–ΒΡ“ΜΟ≈ΩΈ≥ΧΘ§ΨΓΙή”οΈΡ“ΣΆ§―ß–Θ…η÷ΟΒΡΤδΥϋΩΈ≥ΧΖΔ…ζ’β―υΡ«―υΒΡΝΣœΒΘ§ΒΪ”οΈΡΨΆ «”οΈΡΘ§Ή‘”–ΤδΕάΒ±Τδ»ΈΒΡΓΑ»ΈΓ±Θ§±Ί–κ Φ÷’≤Μ”εΒΊΦα Ί”οΈΡ±ΨΈΜΘ§’β“―≥…ΈΣ”οΈΡΫΧ”ΐΫγΒΡΙ≤ ΕΓΘΈ“Ο«ΉΔ“βΒΫΘ§–λΫ≠œ»…ζ≤ΜΒΪ °Ζ÷ΤΪΑ°ΩΒΒ¬’ή―ßΘ§Εχ«“ΜΙΉ‘Ψθ‘Υ”ΟΩΒΒ¬’ή―ß÷ΗΒΦΚΆΗΡ‘λ”οΈΡΫΧ―ß―–ΨΩΘ§Εχ’β’ΐ «–λΫ≠”οΈΡΫΧ―ß―–ΨΩΗΏ≥ω±π»Υ“ΜΫΊΒΡΒΊΖΫΓΘΒΪ“Σ“ΐΤπΈ“Ο«ΉΔ“βΒΡ «Θ§–λΫ≠ΒΡ≤Μ…ΌΈΡ’¬ΦΪΝΠ÷ς’≈“‘ΩΒΒ¬’ή―ßΧφ¥ζ”οΈΡΫΧ―ßΡΎ»ίΘ§ΥϊΤΪάκ”οΈΡΫΧ”ΐ«“Ω¥ΥΤ‘ΎάμΒΡ≤Μ…Ό―‘ΥΒΘ§ΦΪ“ΉΕ‘”οΈΡΫΧ―ß―–ΨΩ”»Τδ «”οΈΡΫΧ―ß≤ζ…ζΗ…»≈ΚΆΈσΒΦΘ§’β «Έ“Ο«“ΣΗώΆβΨ·ΧηΒΡΓΘ–λΈΡΈΣΝΥΥΒΟς“ΐ»κΓΑ ±Φδ“β ΕΓ±ΫβΕΝΈΡ±ΨΒΡ÷Ί“Σ–‘Θ§÷’”Ύ‘ΎΓΕ÷Θ≤°ΩΥΕΈ”Ύέ≥ΓΖΒΡΈΡ±Ψ÷°ΆβΖΔœ÷÷Θ≤°¥”Φ¥ΈΜΒΫΩΥΕΈΒΡ“ΜΗω22ΡξΒΡ ±Φδ≥ΛΕ»Θ§Ψ≠ΙΐΆΤάμΖ÷ΈωΘ§Εœ―‘ΓΑ÷Θ≤°‘Ύ’β÷÷’ΰ÷ΈΕΖ’υΚΆ¬Ήάμ«Ή«ιΒΡΟ§Εή÷–’θ‘ζΚΆΆ¥ΩύΝΥ22ΡξΓ±Θ§ΩΥΕΈ Β‘Ύ «Τ»≤ΜΒΟ“―ΓΘ“ΜΨΌΆΤΖ≠ΝΥΥΈ»Υ¬άΉφ«Ϊ÷°ΥΒΚΆ”…ΥΈ÷ΝΫώΒΡΆ®ΥΒΓΘ≤ΜΙΐΘ§Έ“Ο«‘Ύ’βάο“ΣΧα–―–λΫ≠œ»…ζΒΡ «Θ§¬άΉφ«Ϊ÷°ΥΒ“≤Α’Θ§ ά»ΥΆ®ΥΒ“≤Α’Θ§±œΨΙ «“‘άζ ΖΈΡ±ΨΈΣ“άΨίΘ§ΕύΕύ…Ό…ΌΜΙ”–“ΜΒψ”οΈΡΈΕΓΘΓΑΫΣ œ”ϊ÷°Γ±ΓΔΓΑΕύ––≤Μ“ε±ΊΉ‘±–Θ§Ή”ΙΟ¥ΐ÷°Γ±ΓΔΓΑΈό”ΙΘ§ΫΪΉ‘ΦΑΓ±Β»Θ§ΑΉ÷ΫΚΎΉ÷Θ§ΤώΡήΓΑ≥§‘ΫΓ±ΘΩΕχ–λΈΡ≥ΐΝΥ‘ΎΈΡ±Ψ÷°ΆβΖΔœ÷22ΡξΒΡ ±Φδ≥ΛΕ»Θ§”÷ΜΙΖΔœ÷ΝΥ ≤Ο¥ΘΩ ≤Ο¥ΕΦΟΜΖΔœ÷ΘΓΦ¥ Ι÷ΗΒΦ―ß…ζ―–ΨΩάζ ΖΘ§“≤≤ΜΡή’β―υ―ΫΘ§“ρΈΣ―–ΨΩάζ Ζ «≤ΜΡή“‘Ι¬÷ΛΉςΈΣΝΔ¬έΒΡ“άΨίΒΡΓΘ÷Ν¥ΥΘ§Έ“Ο«≤ΜΡ―Ω¥≥ωΘ§–λΈΡΒΡΓΑ≥§‘ΫΈΡ±ΨΧε ΫΒΡ‘Φ χΓ±ΨΆ «Βδ–ΆΒΡΖ¥”οΈΡΘ§ΥυΈΫΒΡΓΑΉΏœρ’ή―ßΥΦΈ§Γ±Θ§ΥΒΑΉΝΥΘ§ΨΆ «ΤσΆΦ”ΟΩΒΒ¬’ή―ßΧφ¥ζ”οΈΡΫΧ―ßΡΎ»ίΓΘΈ“Ο«≤Δ≤ΜΨήΨχ”ΟΩΒΒ¬’ή―ß÷ΗΒΦ”οΈΡΫΧ―ß―–ΨΩΘ§“≤≤ΜΖ¥Ε‘Α―ΩΒΒ¬’ή―ß¬έΈΡ―ΓΉςΩΈΈΡΘ§≥…ΈΣ”οΈΡ―ßœΑΒΡΕ‘œσΘ§ΒΪ’βΕΦ≤ΜΡήΗΡ±δ”οΈΡΩΈΒΡ–‘÷ ΓΘ“ρΈΣ”οΈΡΩΈΨΆ «”οΈΡΩΈΘ§≤Μ «’ή―ßΩΈΘ§“≤≤Μ «άζ ΖΩΈΓΘ
Ή‘”οΈΡΩΈΗΡ“‘ά¥Θ§–λΫ≠œ»…ζ“‘ΤδΖαΗΜΒΡ―ß ΕΓΔΙΐ”≤ΒΡ”οΈΡΥΊ―χΓΔΕάΧΊΒΡΥΦΈ§ΤΖ÷ ΚΆ’ώ–Υ”οΈΡΫΧ”ΐΒΡ ΙΟϋΗ–Θ§ΖΔ±μΝΥ≤Μ…ΌΕ‘”οΈΡΫΧ”ΐΦΪΗΜΫ®…η–‘ΒΡΚΟΈΡ’¬Θ§»γΥϊΙΊ”Ύ–π ωΓΔΟη–¥ΓΔ¬έ÷ΛΒ»“ΜœΒΝ–”οΈΡΫΧ―ß¬έΈΡΓΘ÷Μ¥ΥΕχ―‘Θ§Έ“Ο«±Ί–κΙΊ–ΡΓΔ’δ ”ΚΆΈϋ»ΓΥϊΒΡ―–ΨΩ≥…ΙϊΓΘΒΪΈ“Ο«“≤“ΣΩ¥ΒΫΘ§”…”Ύ”οΈΡΫΧ”ΐΉ‘…μ¥φ‘ΎΒΡΈ ΧβΘ§”…”Ύ–λΫ≠ΒΡΤΪΑ°ΓΔΤΪΦΛΚΆΫΙΉΤΘ§Φ”÷°≤ΩΖ÷ΟΫΧεΒΡΆΤ≤®÷ζάΫΘ§–λΫ≠“≤ΖΔ±μΝΥ“Μ–©Ε‘”οΈΡΫΧ”ΐΨΏ”–ΒΏΗ≤–‘ΤΤΜΒ–‘ΒΡΈΡ’¬ΓΘΕ‘¥ΥΘ§Έ“Ο«≤ΜΒΪ“Σ ±ΩΧ±Θ≥÷Ψ·ΧηΘ§ΜΙ”Π≤Μ ±”η“‘≥Έ«εΓΘ“ρΈΣΥϊœ÷‘Ύ“― «”οΈΡΫΧ”ΐΫγ“ΜΗωΦΪΨΏ”ΑœλΝΠΒΡ»ΥΈοΓΘΘ®Ής’ΏœΒ«≠ΡœΟώΉε ΠΖΕ―ß‘Κ÷–ΈΡœΒΫΧ ΠΘ©
≤ΈΩΦΈΡœΉ
[1]Άθœ»ω§Θ§Άθ”÷ΤΫ÷ς±ύ.ΈΡ―ß≈ζΤάάμ¬έ θ”οΜψ Ά[G].±±Ψ©ΘΚΗΏΒ»ΫΧ”ΐ≥ωΑφ…γΘ§2006
[2]≥¬ΙϊΑ≤.ΗΏΩΦΉςΈΡΕ‘ΈΡΧε”ΠΉς Β±ΒΡœό÷Τ[J],ΚΰΡœΫΧ”ΐ,2006(1)
Α≤―τ
ΓΨ”οΈΡΕΝ–¥ΫΧ―ßΡή≥§‘ΫΈΡΧε¬πΓΩœύΙΊΈΡ’¬ΘΚ
”οΈΡΫΧ―ßΧΐΥΒΕΝ–¥Ε·Χ§ΡΘ ΫΦΑΖ¥ΥΦ07-07
ΓΕΩ’ΤχΡή’ΦΨίΩ’Φδ¬πΓΖΫΧ―ßΖ¥ΥΦ10-24
ΓΕ«ß“‘ΡΎ ΐΒΡΕΝ–¥ΓΖΫΧ―ßΖ¥ΥΦ09-21
«≥ΧΗ≥θ÷–…ζ”οΈΡΕΝ–¥ΡήΝΠΒΡ≈ύ―χ10-24
ΓΕ100“‘ΡΎ ΐΒΡΕΝ–¥ΓΖΫΧ―ßΖ¥ΥΦΖΕΈΡΘ®Ά®”Ο11ΤΣΘ©06-23
”οΈΡΉέΚœ ΒΦυΜνΕ·--Άχ…œΕΝ–¥”κΫΜΝς ΫΧ―ß…ηΦΤ(Υ’ΫΧΑφΤΏΡξΦΕœ¬≤α) ΫΧΑΗΫΧ―ß…ηΦΤ08-14
ΓΕΑΌΖ÷ ΐΒΡ“β“εΚΆΕΝ–¥ΓΖΫΧ―ßΖ¥ΥΦ10-26